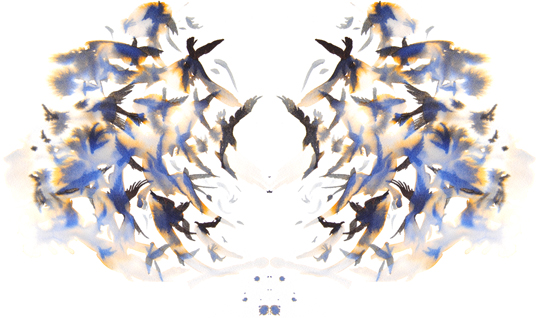蜜蜂变少了。蜜蜂之前,萤火虫变少了。有一天佛朗明哥粉红鹤(弯着长脖子,单脚站立,看上去昏昏欲睡的那种)出现在我梦里。从一只,突然增加到无限多,整齐列队如矩阵,纪律严明。鹤们无声地在我的梦里说:要向Hello Kitty夺回粉红色的所有权。
向右是红,向左是白。中间是粉红色。被少女与模仿少女的名媛们使用到泛滥的颜色。被Sex and the City化了的颜色。想要美艳又想要纯洁,不敢当红玫瑰又不甘心当白玫瑰。佛朗明哥粉红鹤你们若要一一申诉侵权,恐怕会树敌太多。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人类能拥有的颜色很少。其中没有粉红色。
那时,夜还很黑。星星能被看得清楚。不是一颗一颗,而是一组一组地看见,兽,龙,鸟,女人,鱼,猎手。地上没有其他的光了。除了屋里的灯,城头的火,城外野地少数少数发光的物种之外,一片漆黑。因此入夜后天上的世界,比地上具体得多。
萤火虫是边境的光。在河岸,水与土交壤的地方,在沼泽,湿地,生物犹疑不定,该用腮,还是用肺呼吸;必须游水,还是行走。在那暧昧的地带,有虫光微微。微光将黑暗浸湿,软化,渗透到它的最内里。于是在黑暗之中就包藏了光的源头,人便受到抚慰。即使在云翳遮掩了星光的夜里,人还能看见萤火虫为人拟态的星星。凉凉的微明。未知之中的具体。
这个故事里的人看见了萤火虫。在他体内他看不见的体腔某处,好像也亮了一下。萤火虫模仿星星,他的细胞模仿了萤火虫。
距离水岸更远的地方,也有光。是磷火,又称鬼火。那里,土地已经远离了水岸。生物摆脱了两栖的犹豫,长出地面重力环境需要的骨骼与肌肉,变得坚定。这个看着萤火虫的人,用同一双眼睛,又看见了磷火。他已经知道,在磷火的下方,有一具尸骸。虽然现在,因为距离与深黑夜色的缘故,有形的白骨是不可见的,只有气味般挥发飘忽的光。有时他有这样一种印象:死亡是光亮的,活着是黑暗的。
他认识那具骸骨。当骸骨还拥有肉,血,与一个人的名字时。
蝗虫
人不是人。战争决定谁有资格当人,谁要被坑埋到地下,谁的故事会变成历史,谁的女人能保住她产下的孩子。
那一年,蝗虫从东方来。
"这是意念的攻击。意念的攻击之后,才会是真正的血肉相搏。"
单独一只是蚂蚱,绿色,趴在芦苇上,啃叶子吃。一个小孩伸手指轻轻一捻,就把它从草叶上抓下来。小孩玩蚂蚱,听到妈妈喊"吃饭了",就捏死它,扔掉。
不知在哪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蚂蚱过度繁殖,数量到达一个临界点,它们就变了,集体发狂了。蚂蚱长出霸凌者的肢体与暴烈的攻击性,甚至能吃掉动物。它们和原来那些吃青草的小虫子,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这一切只是因为,同类的量多了,密度高了,相互紧挨着摩擦着,这些小虫子的胆子就大起来了,性情都变了。就像人聚居在城里一样,再也不会和住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一样了。
"这,就是你即将面临的顽抗。就为了对抗你嬴秦这一个国家,东方的六国会团结在一起。这些,来自东面如尘土般的人,会化身成一头组合兽。燕国的翅,楚国的身,赵国的眼,齐国的骨。"
嬴政,15岁,心知肚明,有过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头组合兽,就是他亲手毁掉的那种。
鸟
一头悬浮的鹰。气流带着它上升。它在等待,还是在观察。或者都不是。此时这悬浮的状态便是它存在的全部。如同有些生物,在某个季节时,不断交配是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它能感知在每一根羽翼的四面八方,气流的方向。它能感知身内空洞的体腔,正与身外广阔的天空进行着对话。空翻译着空。
它听见来自十方上下,其他鸟类的声音。这许多藉空行走的同类,有的翅小,低飞,振动击空的频率高,尖锐,吵闹。有的翅大,飞高,翅膀久久才掀动一回,却影响着气流的方向,像在空气中留下了爪印。当一个爪印产生了,它总能察觉。于是它将身体旋入气流,拍了几下翅膀,向远方一只大鹏鸟致意。
越过山头,鹰开始降低高度。触地的瞬间化为一男子,有一头白发,与一张年轻的脸。
最初,秦人的祖先在东方,看守日出。后来他们迁到西方,看守日落。秦人的祖灵,化为群鸟,分散在东与西之间。任何一个个体,都在自己的地球经线上,看守那条线日夜交换的时刻—时间是一条接缝。站立点在接缝的哪一边,却有可能彻底改写一个文明。在极东它们迎接破晓,在极西它们迎接夜闇。
群鸟听说过,也感觉得到,在山的那头有别的神人看守日落。它们谨守本分,不越界,向幽冥之中,另一神异的存在致意。只知道,山那边的神人和它们完全不同,不同到甚至不能共存在山的同一边。既然如此,距离便是最好的致意。
有各种关于那西方神人的传言。有人说是一只老虎。也有人说是金色的人种。有人说他是秋天之神,是职司死亡,典管刑杀的神。当他出现,就有是非,有对错。有了对错,人便会犯错。无人能永远不错。于是人们永远都在恐惧,严厉的惩罚将由神人降下。但没人逃得过。没人能不经历神人带来的成年,老去,死亡之过程。人成年了就得为对错负责。人老了病了将死了就觉得是受了惩罚。人死了,就被那神祇引入幽冥。一入幽冥,就不是我们在生之人讨论的范围了。
据说生与死是模糊的。我们有可能死了却没发觉。没有声音从那里返还过。死者把声音留下了。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等待与他生前有约的人,终于也来到死亡之谷—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再也不能爽约了。
祖灵不知道,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事态已发展到超越他们理解的范围。在赢政之前,每一个秦王的灵,现在都是鸟群的一部分。它们只是暂时化身为人,一回神又变成了鸟。但这嬴政身上有什么,正彻底地改变着祖宗章法,灵体的形状。这已经超过他们能知道的范围。它们知道时间。它们知道生命会在时间中朽坏。灵会回到鸟群之中。他在世时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一趟资料收集,为集体增加一个运算用的变量。
能做的只有守望而已。而守望,只是等待而已。
日落,西方骚动。由鹰化为的男子,站在山的棱线上倾听。他好像了解,又好像不解。那是来自山的彼侧,死者的声音。死者是顽固的守候者。他们可以无尽地等下去。他们发出的,只是些一再重复的回声。
嬴政能抵挡重复吗?你能抵挡重复吗?人类能抵挡重复吗?
男子跃下山棱。他的身体像一滴雨水落入大海般融入山顶的气流,他的双臂已经化为羽翼,他又是一头鹰了。
人
嬴政13岁,继立为秦王。
权力之前,是死亡。王位必然是死亡的产物—嬴政的爸爸死了,他才成了王。
13岁太年轻?其实还好,大部分的事情,有吕不韦搞定。这个吕不韦一直挺他,为他杀掉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因为,他从吕不韦的眼神里读到,他的王位继承权不容威胁。
外头有人说,弟弟被杀,是因为他不是秦王的亲生子,而是王妃出轨的野种,活着一天就是一则会走路的王室丑闻。
"绝对是吕老头放的风声。"第一次有人在嬴政跟前耳语,他就这样觉得。吕不韦会在意秦国王室血统的纯正性,女人的贞操,鬼才相信。那个来向他传递耳语的人,是个阉人,负责伺候他起居。每天早上嬴政更衣时,他会带来前一天宫里发生的事,流传的消息。他几乎对这阉人生出一种依赖感。毕竟这是进宫以来的每一天,他睁眼第一个见到的人。夜里他被幻象与梦包围,天渐亮而他将醒未醒,蒙昧不知身之所在。这个阉人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更衣,唤起他皮肤的感受。说话,把他的世界放进语言的盒子里,他就又有了身份,来历,规矩。
"听说,那根本不是王的孩子。您想,这传出去,大王的脸面往哪摆?因此吕大人只好杀了他。王的尊严是要保全的,否则不是乱了嘛。您,才是大王唯一的儿子。您是太子呀!"
他立刻就警觉了。"是吕老头放的消息。"但他只嗯了一声,看了那阉人一眼。在那一眼中,他竭力隐藏着他的诧异,与厌恶。直觉告诉他:"是吕老头让他来说给我听的。这个人,是吕老头的人。"只一秒,他的眼神便飘开了。从此他看这个阉人时,不再带任何感情。
嬴政不介意有个弟弟。但是祖母很疼这个弟弟,这就使弟弟不只是个小他几岁的男孩。弟弟危险,必须得死。嬴政学会:疼爱是危险的,必须铲除他没得到的疼爱,才能保护自己。
他还记得,刚从邯郸来到秦国时,被带去拜见祖母夏太后。夏太后让弟弟坐在她膝盖上,受他和母亲的大礼。
那时他的父亲异人,原在赵国当人质的,已经潜逃回国,继承王位多年。他和母亲在邯郸等待着机会,等到返回秦国和父亲团聚的一天,等待由阶下囚一变而为王后和王子,等待着一个不知是否会被辜负的承诺。他一直被教导,有一个在他方的自己,一个更高贵、更富有、什么也不必怕的他。一个在他方的身份—秦王之子政,像一只寄存行李,等待他去提领。
弟弟是在那段时间出生的。当他的身份还被寄存在远方时。弟弟出生了。他是不曾和父母分开过的孩子,出生就住在王宫里,并且还拥有一位祖母。嬴政没有祖母。当他伏在地上,仰起头看见夏太后冷淡的脸孔,当下知道,他没有祖母。
祖母一出现,弟弟就会用小孩子的鼻音说话,明明都已经过了那年纪了,还装。那一脸的天真,也是在装傻。太后竟然都看不出来?不论弟弟说什么,太后都笑,都夸。太后一离去,弟弟就恢复一脸傲慢与冷酷。那天,他第一次感受到的情绪,有人说是嫉妒。但他觉得,他只是讨厌那种幼稚的伪装。这个被过度溺爱,在保护下长大的孩子,没有像他一样经历过,异国漫长的等待,没把这个哥哥看在眼里,低头继续玩他的合金玩具—一只青铜兽。
爱是奢侈品,应该被严格管理,实施配额制。爱,弟弟一出生就有。但嬴政知道,这也是吕不韦想要他相信的:只有他才够资格拥有奢侈品。僭越者,死。
生宫
王位,性命,身份,都不是稳固的。没有什么权力是天赋的。都是挣来的。我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连我是谁,是谁的孩子,都可以被篡改。我父亲就是个例子。
我的父亲秦异人,是秦国太子的儿子。
当时的秦太子,我的爷爷,后来的秦王,娶了很多太太、生了很多儿子。多到再多一个不算什么,少一个他可能也不会发现。孩子多可以提高把DNA留在世上的机率。对爷爷而言,这是个机率问题。
但对爸爸而言,却是押上了他整个人生的问题。在爷爷的一大堆儿子中,我爸和他的一大堆兄弟中,只有一个人后来能成为太子、再后来会成为王。
除了这个被选中的未来的王,其他儿子都可以被拿去交易。
异人就属于可以被交易的。他的母亲夏妃不是正宫,又不得太子欢心,他被封为太子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异人也不够出脱,给太子的印象不深。有一天秦国和赵国的大臣在外交会议上吵起来,互相威胁着要用军队打烂对方的城墙、田地、宫殿和宗庙。威胁完对方后他们又有志一同地回国勒索自己的王,建议送个小王子去对方国都当人质。
几个内官和外官聚在一起讨论了一阵,提交建议人选供王与太子批可。最有办法的王子们能得王与太子的宠爱,不会被列入。次有办法的王子们,也都运作了官员,让自己不要被列入。异人属于第三种,被列入的那种。
临行前,他去给太子辞行。
"你叫什么名字?"太子问。
"我是异人。父亲大人。"
父亲这个称谓,在太子心中激起了亲密的情感。他有点惭愧,竟忘了儿子的名字。他拉起异人的手,劝了几杯酒。这几杯酒使得异人一上马车就睡着了,使他在昏沉中离开故乡,没流眼泪。
焦虑是到了赵国之后才开始的。要是和平能够担保,也用不着派人质了。秦赵要打仗的风声从来没少过,一有事异人就担心士兵破门而入,把他抓去受酷刑。异国异乡异地,他看不出自己这个担保品有什么价值。战争一旦爆发,没人会把他的性命当回事。除了他自己。
异人觉得死在乱军阵中,好过作人质。人质的死,是最孤独的死。军队还没开打,就被单独叫出列,一个人受刑受死。在群体之中是安全的,生命本来就应该以量取胜,要不是他父亲有成群的精子向卵子游去,他被生下来的机会就微小了。生从精子堆中生,死也该死在人堆里。一个人的死太叫人害怕。至少异人是这样想的。
第一个对他说,他不必日夜担心生死问题的人,是吕不韦。
"你看看,你可是王子哪,"吕不韦大声说,"你不想死得孤单,但也不必躲在人堆里。你,你是王子哪。"他的口气好像在说异人有多不识货。那时异人脑中出现的画面,是电视购物频道主持人,他是被展示的货品。
吕不韦有这种能力。他是个商人。他的能力是找到货物,让货物的价值翻倍,而后出手。这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能力。吕不韦称为"钓奇",从寻常的货品中,找到够奇、够珍贵稀有的理由,让石头被点成黄金。
后来大家都说吕不韦眼力好,识货,收了异人这一路看涨的好货。真是一单好买卖。吕不韦只是笑笑。其实异人不是他的第一笔货物。赵姬才是。
传说中,吕不韦是我第二个父亲。也有人说,他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知道人们都是怎么说的,说是他先把我像种子般种在女人的身体里,然后再把女人送到异人那里去。像寄生蜂总要在其他昆虫的体内产卵,借着宿主的养分壮大。我身上带着吕不韦的DNA,进入秦朝的王室,成了他们的子嗣。
他们说吕不韦为我做了那么多,是因为他真正疼爱着我。谁知道。商人不会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谁知道吕不韦是不是还产卵到其他王室。只不过,产在秦王室里的这个我,先孵化了。
那些来不及孵化的,当然也不会被写进历史里。你懂吗?没被写下的历史,没有孵化的计划,比被写下被孵出的多太多了。
我们都像寄生蜂。吕不韦为我父亲异人谋划的大计,也是一种寄生蜂型的战略。他看准了问题的关键,父亲不够特殊,才会成为人质。父亲该做的,不是更往人群里躲,希望大家忘了来杀他,而是做好个人形象。"要活命,就得变成你父亲心目中唯一特殊的儿子。他真正的子嗣。"吕不韦说。
"怎么做?"父亲问。这个一直想躲起来的人,从没想过如何争宠。
"你父亲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你去当她的儿子。"
在我和我父亲的时代,儿子,是可以后天人工合成的。吕不韦在幕后操办。让异人认了华阳夫人当义母。
异人的生母夏妃,失丈夫之宠在前,儿子认人作娘在后。在女人的战争里,她已连输两盘。但我祖母不是普通的女人。她压下愤恨,卑微地恭贺华阳夫人,得此子嗣,真真是个好子嗣。
从此我的父亲异人成为寄生蜂,寄生在秦太子与华阳夫人身边。而他的母亲夏妃不动声色。不到最后,不知谁才是真正的蜂后。
华阳夫人是楚国公主。你可以说,她也是只寄生蜂。是楚国送到秦国宫里的一只蜂。或许这是为什么,华阳公主愿意让异人寄生。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目标。她没孩子。得宠只是此时,她需要把自己的未来寄生在一个秦王子身上。她认出她的机会。这是一个未来的势力,她可以培植。
这是吕不韦的机关算计,也是华阳公主的算计。是他把异人送去给她,也是她选择了异人。是他将异人这枚卵植入太子与华阳公主的婚姻,也是她作为楚国公主往秦王室里产卵。她或许不知道,这枚异姓之卵会孵化出什么,或许会生出个反弑她的怪物?但她已作好准备。
现在想来,当时已埋下争端的种子,后来发育熟成,产出一桩血案。我就是寄生蜂的孩子,血案的执行者。
世界要关门了。前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有预感的人们都在设法找宿主,寄生到权贵之家,让血脉受保护,基因传递下去,同时带回权力与财富。他们交媾,他们交易,他们梭哈了手上的筹码,想在下个崭新的时代里占尽先机,翻出红盘。在华阳夫人的家乡楚国,进行了几乎一样的寄生蜂实验。春申君让歌女怀孕,把怀孕的歌女送进宫。他没有成功。他甚至没看出来,歌女爱的是她哥哥。那孩子,是这对畸恋的兄妹凭借宫廷权力斗争的掩护,产下的近亲乱伦的血胤。
死宫
读到这里或许你会懂,或至少对我有一点同情。虽然我并不稀罕你的同情。你会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几乎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我已经忘记自己真正的来历,或许我从没记得过。我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版本:秦世系里记载的,还是吕不韦想要我相信的;我父亲说的,还是夏太后冷淡的眼光里暗示的。我是谁的孩子?也许我应该问我的母亲。但她从很久以前就不跟我说话了,在我杀光她所有情人以后。
有一次我闭上眼看到了海。我一辈子没看过的,没有尽头的水域。
看到那画面时,我好像忽然知道了,懂得了什么。就像是有人在我的脑里放教学片,我的脑子就是他放映的布幕,没人说话,但我忽然懂了。
"现在无关紧要。未来,未来才是一切。"
"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会消失。我认识的人都会死。只有未来,不管是什么样子,一定会发生。"
我想去未来。我想要参加未来。我想要在未来的某件事里。
即使未来是死。
那以后,我看见眼前走动的人,现在活着的人,我会想,这是一群未来的死者。我已经看见他们死了。我穿上黑衣。我让黑色成为秦国的国色。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在祭奠他们,超度他们了。死是归宿。死不可悲。至少,在我还没感受生之欢愉以前。
生之欢愉,是吕不韦教会我父亲的第一件事。
"你这个地位的人,应当过得享受些。"他说。
"比如女人。"吕不韦说,眼睛盯着异人,瞳孔放光。"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必须是个好女人。好女人可没那么容易找哦。"
说这话时,吕不韦用很慢的动作,将赵姬的衣裳一件件脱下。
刚帮异人斟满酒的侍婢,放下酒樽,伏低了身子,包覆住异人的阳具,先用手,后用嘴。
赵姬身上又一件衣服滑落。
"你看,这女人是不是很美?赵国的女人不但美,而且赵国知道怎样教养女人,教出会伺候男人的女人,会让男人年轻十岁的女人。这种女人会让男人放下干戈。但男人也会为这种女人打仗。"
赵姬已经一丝不挂,脸也不红。吕不韦把手指伸进她的阴户。"异人公子你看,这是上好的女人,随时都是湿的。"吕不韦把赵姬放倒在席上,手指抚摸她的阴户。
赵姬闭着眼发出舒服的喉音。吕不韦手指的动作很慢,滑入,又滑出。异人说不出话来,他的阳具已经膨胀得发疼。他一边馋着赵姬,一边佩服着吕不韦。真是个高手。
"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人玩。"吕不韦站起身,说:"好好伺候公子。"他抓住正在帮异人口交的婢女,带着她转到屏风后面去了。
赵姬又光又滑的身子靠过来。他拦腰抱住。赵姬简直周身无骨,缠在他胸前,就像一件夏衣。她腰腿一扭,已经滑进他衣服里,大腿熨帖着他的阳具。
太舒服了。他忍不住从喉头迸出声音。
推走酒食,压倒美人,一阵云雨狂乱。
吕不韦在矮屏风后看着他俩媾和,一面让刚才的婢女为他口交。这老狐狸。异人心里骂着,但吕不韦那窥淫的视线却让他格外兴奋。赵姬也越发狂乱,眼神迷蒙,他觉得好像认识她好久。一种回到更古远的时代,基因里的记忆,当两人都还是野兽,不,更远,还是两只三叶虫的时候。交媾。就是交媾。太舒服了。忘了为什么。忘了身份,忘了国与国,忘了什么以物易物,奇货可居。
异人看见灯光在屏风上映出的人影形状。胖大的吕不韦,抓着娇小的婢女的腰肢,一下一下地顶,肚子撞在女孩翘起的臀上。
异人接受吕不韦送给他的女人,也接受了吕不韦这个盟友。吕不韦会的,他也都学会。
华阳夫人派来了使者。年少的楚国贵介子弟,带着第一次出任务的小题大做,没吃过苦的理所当然。当晚异人以赵姬款待他。这次他把自己放入吕不韦的位置,成了屏风后的观看者,饱经风月的老手,能超越情欲地占有,能分享欢愉的人。
少年由惊慌失措,而意乱情迷。次晨当他要离去时,已经对异人充满感激,感激他带他进入这个成年人的、没人告诉过他的世界。感谢他无私的分享。那是一回毕生难忘的体验。如此成熟妩媚的胴体,如此胴体带给他的欢愉,后来他在楚国再也不曾经验到过。到他只能与死人为伍的时候,这是他最有生气的回忆。他一遍一遍回想。回忆让他感到,自己与死人还是有一点区别。
从那时,来到了现在。从邯郸,到了咸阳。从我母亲与出入我母亲身体的男人们到我。无数一冲向前的精子里只有一个,它的DNA被留下来。在我体内。我,15岁,计算着在六国攻来之前,我能召集多少兵,有多少力量能用。怎么能让力量更大。能让一个兵有不止一个兵的力。人是怎么演化出这许多力量,与对力量的需求的?当还是一枚精子时,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向前冲,这唯一的,转瞬干涸的力量而已。
敌人多吗?
"多。秦国以外都是我的敌人。我以一国敌六国,还不算那些小国家。"
"集体是一种错觉,"我的国师说,"六国是敌人。你不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敌人。他们是六个国家。你也不要把他们当作六个国家,他们就是很多的人。随便看都是一个人,他一个人,你也一个人。"
有这么容易就好了。
蝗虫来了。阉人瞒着我,不告诉我,可是我能感觉到。从天空的另一端,像乌云般过来了。从梦里惊坐起,听到的声音像是梦境的尘埃碎裂飘浮在空气里。恶魔在拍翅。它们来了。
我甩开侍卫,跨上马,冲到城外。它们来了。巨大的饿红了眼的蝗虫撞在我身上,脸上。钻进我袍里。前仆后继地。它们的飞翔里有一种疯狂。不是为了吃。甚至不是为了要活。是为了要死。
我需要力量。能杀死这些虫子,削弱它们,能让它们远离的力量。此刻就有一种。有一种力量在我体内如云般生起。人真的想要力量的时候,能得到自己想不到的力量。或许从那一刻起,我也变了。我的基因变了。像闹灾的蝗虫不再是蚂蚱。我不再是秦王室,玄鸟的后代。我是一个容器,盛接着我从不知处借来的力量。
鹰人在远处看着嬴政。他站在平原中央,承受阵阵蝗虫的击打。在鹰人眼里,嬴政的神情也是疯狂的。被这些疯狂的虫子唤起了,鹰人不知道的力量。鹰人感到,那是从山另一边借来的力量。它与秦国的祖灵们没有发言权,也阻止不了。不知道会将秦人带往何方。在它们统治时,从没走过这么危险的棋。如今它们虔诚地等待着让命运揭示其后果。
起雾了。
黑色的蝗虫,飞入乳白色的雾中。不知过了多久。不知早晚。日月都受了障蔽,看不见。这就是光的缺陷。光总是会被障蔽的。
从浓雾深处传来低沉的吼声。像虎,或豹。兽的声音。令鹰人为之战栗的声音。战栗使它放弃了人身,以鹰的身份飞走。
浓雾使蝗虫变形。浓雾障蔽了它们,使它们不知道同类就在身边,以为落了单,以为要打群架但伙伴没跟上来。蝗虫切换回素食胆小的绿色虫子,单独行动时的模式,又温驯了。或许温驯始终只是假面,所以能这么快戴上。反之亦然,凶猛也是假面。假面的蚂蚱,被雾深处一股沼泽的潮湿气味吸引,前仆后继扑了去。水面上,有雾气疾走而来,苍色大蛇般的形体盘在河上,张开口,蝗虫全都飞进去。
那年秦地的农作歉收,但河川鱼虾盛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嬴政的军队得到高蛋白的伙食补给。而六国军队不堪一击。好像他们的魂魄早已在某处被吃掉。战场不是结局的现场。
我母后为秦国组织起蜂巢般的结构。东方六国没人知道,秦国强大的秘密。蜂群的中心,是蜂后赵姬,我的母亲。从赵都邯郸来到秦都咸阳后,她的性史。她拥有众多的情人与面首,日夜交配,她的情欲越激发就越漫流,高潮的次数越多,秦国庄稼便越是丰饶,争战便越是常胜。她是胜利女神,也是我的母亲。但我对她的胜利只是疏离。总觉得那胜利不是真实的,因此不可能是永远的。生之外,还有死。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已经用死亡重新结构了帝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