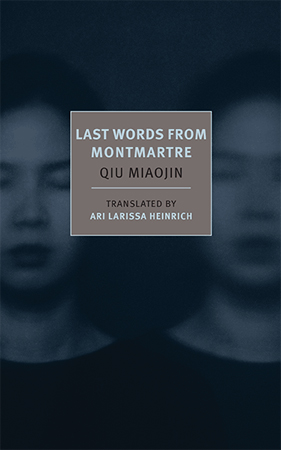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位早慧的二十六岁臺湾小说家,邱妙津也加入了这些殉道者的行列。由於受抑鬱困扰,邱在她巴黎的寓所用一把碎冰锥刺入心脏(一说餐刀,而这自死的谜团甚至也成为了她传奇的一部分),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就在邱妙津离世後不久,她的第一部小说《鳄鱼手记》就获得了臺湾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时报文学推荐奖」。而在她身後出版的《蒙马特遗书》,这本带有半自传色彩、书信体的小说已然成为了一部受到狂热崇拜的经典之作,在臺湾的同志群体之中尤甚。用臺湾小说家骆以军的话来说,《蒙马特遗书》是「一部女同志的圣经」。《印刻文学生活志》曾出版纪念专刊,记录她的生命轨迹并刊登了她的作品。无独有偶,骆以军的《遣悲怀》与赖香吟的小说《其後》也均为对她的致敬之作。纽约书评最近出版了由艾理·乐丽萨·海因里希翻译的《蒙马特遗书》(2014),并将於2015年出版由许博理翻译的《鳄鱼手记》。纽约书评对其作品的出版将她的作家身份置於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纽约书评的「经典系列」之中,除她以外,只有一位汉语作者,便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盛名的作家张爱玲。
《蒙马特遗书》这部小说共百馀页,包含了二十封信件,叙述者均为一位在巴黎求学的女性,它们有些没有特定的收信人、有些寄给她的朋友或家人、还有些为她的挚爱,一个叫做絮的女子所书。在这些信中,叙述者记录了自己在巴黎的留学生活、1995年雅克·希拉克的当选,谈及安哲·罗普洛斯的的电影、安部公房与太宰治的作品,阐明了她对性别认同的态度,透露了她自死的念头,更有甚者倾吐了她所有的热望。读者们被告知能够以任何顺序阅读这些信,然而无论是正序或倒序阅读,随著小说的行进,时序和人称都愈加混乱。寄信人有时候是Zoe,以阳性而强势的口吻叙述,而有些信又像是絮写给Zoe的,有些信则全然不像是信。但事实如何根本不重要,因为推动小说发展的是激情——一种炽烈迫人的激情:
絮,你不知我是如何在爱著你,终我一生我都会在这里,我都要如此爱你,你不明白我是如何在爱著你,或说你不愿明白......你看轻我及我的爱之价值,使我溃烂,然而,我会用我一生来證明我自己的美与爱,用一个「不朽者」的我来使爱闪闪发光,我会使你明白这一切才是生命的终极意义的。然而,我不再述说这种意义了,从此我保持缄默,上天会使人们领会我的,而你也会是那当中的一人......
从语言角度来说,邱的中文措辞略显深沉,但绝不艰涩,而正是这般深沉的措辞,这隆重而又形而上的陈情,赋予她的热望以重量。通过短句反复地逼近与衝击,佐以现代主义风格的长句,她激起了一种摄人心魄的狂热。《蒙马特遗书》的译者,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教授,艾理·勒利撒·海因里希被誉为学者型译者中的佼佼者。他对邱的作品非常熟稔,因此在翻译时準确地用英文还原了书中出现的文学引用,包括:西尔维亚·普拉斯,凯西·阿克,爱莲·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凯斯·科恩与宝拉·科恩译本),以及让·热内(贝纳德·福莱希特曼译本)。
多亏了海因里希精准的翻译和对原文的把握,邱妙津的激情,她那汹湧而坚定的情感才能在译文中完整地重现。邱妙津的字字句句对读者之衝击有如一场海啸:以其不高的势头,缓慢却準确无误地向岸头奔湧而来,湮没了地表的每一条罅隙沟壑,动摇了地面的每一人一物。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激情」,而是中国人所谓的「情」,一种勃发於成熟美学思想的激情。为「情」所困之人,会将其视为生而为人的必要条件。正如十六世纪中国戏剧《牡丹亭》的序言中所书,情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若将此种激情与九十年代初臺湾社会中的同志欲望联繫在一起,则能读出强烈的政治意味。一般而言,现代中国和臺湾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仅仅建立在同志"不现身"的前提之下。正如学者刘人鹏和丁乃非所言,「恐同的力量并非像西方那样以暴力和直接的形式运作,而是为了保全他人的面子(那些循规蹈矩之人的面子)。」《蒙马特遗书》可以被视作是影射此种社会政治形势的寓言。就像那些收件人未详的信件,邱妙津的小说展现了其身为同志,对得到臺湾社会认同的强烈渴望。像邱妙津这样的年轻人,毕业于臺湾的顶尖学府,拒绝保全面子,反之却用「情」的力量将面子彻底粉碎,这无疑是为同志解放作出的一记无畏的反击。
《蒙马特遗书》的故事在海峡两岸同时掀起的学运政治浪潮中结束。1919年数以千计的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在国际事件中的软弱作风,现代中国在五四运动中神话般地诞生。自彼时起,青年学生在中国就一直扮演著特殊的政治角色。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下,青年,特别是学生的旺盛生命力,便成了中华民族兴邦振国的根本基础。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就曾做过这样的譬喻:「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在1989年的北京和1990年的臺北,当数以千计的学生为了国家的民主上街示威遊行,他们对当局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威胁。邱妙津拒绝继续隐瞒其同志身份,恰与中国学生们拒绝默默无言地接受当局加於他们的政治角色相呼应。在这本小说的封底上,有当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领袖(後被政治流放)王丹的推荐语,他称感到自己「从第一页起就与邱妙津之间产生了某种隐秘的联繫。」
对这部作品的政治注解亦是对书中伦理问题的强调,因为天安门事件和野百合学运也包含著殉道政治。在接受一位美国学生的采访时,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柴玲有一句著名的回答:「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後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同样,《蒙马特遗书》的叙事者也很清楚,她的人生旅程会以自我牺牲而告终:「我决定要自杀,以前所未有的清醒、理智、决心与轻松,因为是为了追求关於我生命终极的意义,是为了彻底负起我所领悟的,关於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责任......」
这种殉道也许表现了政治和哲学上的严肃性,这种殉道甚至也许是必要的,但它无疑也是自私的。这本小说不单记录了被压抑的激情,也记录了激情的背面之物:抑鬱。抑鬱并非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面对痛苦的一种正向衝动。和「情」一样,它来势汹湧,弥漫了整个世界。这样强烈的情绪几乎没有为他人的存在留下馀地,即便是那些你最珍惜之人。《蒙马特遗书》的叙述者并未多加考虑她所爱之人,絮,要怎样面对她的自死。事实上,贯穿全书,叙述者只对絮的欲望作了极为短暂的聆听。重读上文那段摘录,若将之看作是一个男人在追求一个女人时的告白,你会发现这是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一个女人被告知,在另一个人的欲望面前,她该有怎样的感受,该做出怎样的回应。
将自死的抑鬱之情,或是年轻人那种激昂的狂热解码为一种美学政治,是个棘手的任务——也许我不该做此尝试。我发现自己被《蒙马特遗书》中描写叙述者在巴黎日常生活的片段所深深吸引:
留了一通电话在翁翁的答录机里,告诉他我已看过《重庆森林》及《爱情万岁》的感想。傍晚回家做了一盘洋葱蛋炒牛肉,通心粉,煮了饭,看电视新闻,之後就回房间把那叁十组邮票贴在写好的信封上,边听你寄来的歌剧精选,感觉奇异地幸福。
毫无疑问,《蒙马特遗书》是震撼人心的。它影响了臺湾同志群体和整整一代臺湾反叛者、边缘人的原因已毋需多言。我期待这本书精准的英译本会吸引一个全新的读者群。但在这本小说中,最令我动容的并非邱妙津自杀的悲昂诗篇,而是她一生的平淡行文。小说还暗含著另一个寓意: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因不被社会认可而消沉,被巨大的抑鬱所压制,每日却仍艰难地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多博取一天。这原本也能成为邱妙津的人生传奇,不幸的是,这个传奇已再无续写的可能了。